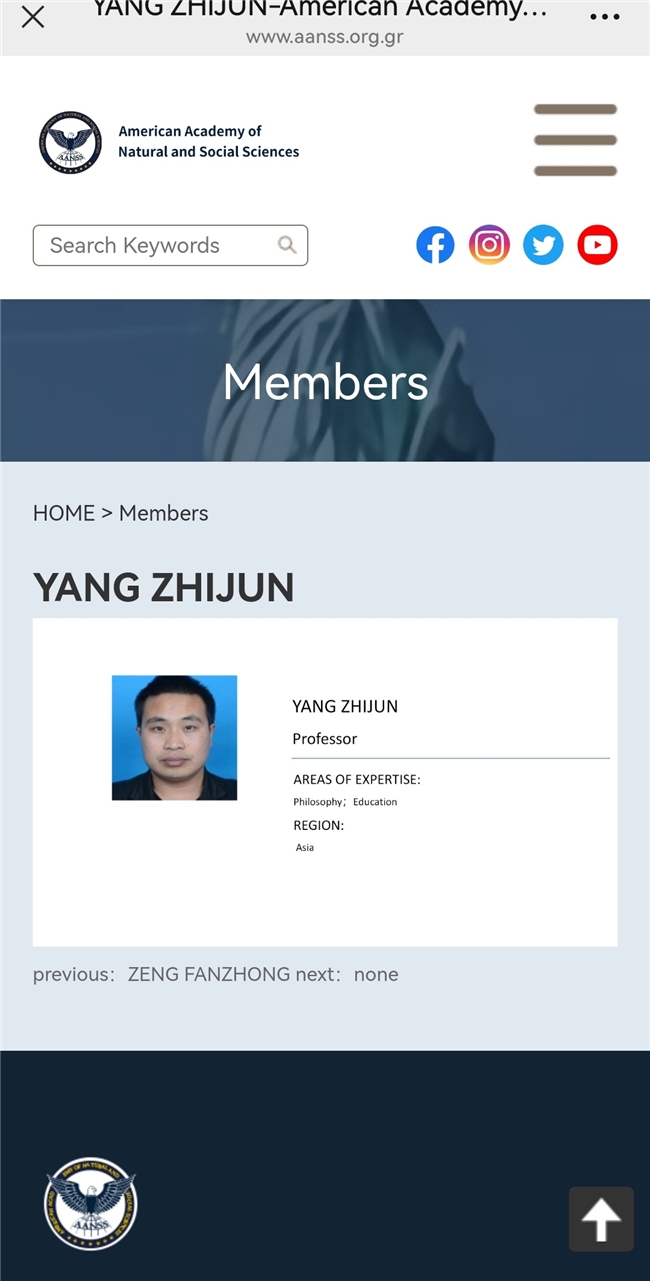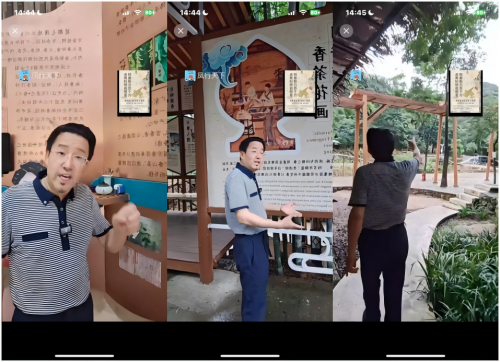个人档案与公共记忆
——郑曦原《选调生》的非虚构叙事
翁礼明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产品,始终滋养着每一个追求意义的灵魂,始终烛照着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
为了彰显文学家对历史发展的洞见,往往将文学成果与虚构相关联,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文学之所以具有通透性、前瞻性是因为文学家具备一种超乎寻常的历史眼光,能够触摸到历史发展脉搏,而这种能力恰恰源于文学家具有超乎寻常的虚构能力。
然而,世界文学史的历史经验证明,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许并非虚构性叙事,而是在写实基础上对历史的真实记录。
古希腊最大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在经典文学史家的眼中无疑是对古希腊神话的记录,而神话本身又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文学。然而19世纪的德国商人海因里希·谢里曼童年时期深爱《荷马史诗》并坚信这一伟大作品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这一童年执念支撑他在中年经商发财之后,在古希腊的废墟上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终于于1873年谢里曼发掘出“普里阿斯宝藏”,1876发掘“阿伽门农具面”。谢里曼异想天开的想象力和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将世界文学史的经典作品《荷马史诗》推到了信史高度,为人类重新定义文学与史学提供了难得样本。
以文学的笔法真实记录生活事件,《荷马史诗》并非孤例。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因为无力支付裁缝布依松的工钱,答应将布依松的裁缝店写入他的小说之中,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巴尔扎克多次提及“布依松裁缝店”。这种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交织,使文学不仅承载着人类的情绪情感和精神追求,而且承载着特定时空的人文历史风貌,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注入了虚构作品无法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核。
郑曦原的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文学笔法为手段的文学随笔《选调生》,在文学的真实性和真实的文学性之间寻找到一种全新创作路径。《选调生》以266篇日记和23封书为基础,以个人经验和个体感受为核心,通过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刻画,形成具有私密性与反思性的文本档案,同时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选调生》以日记体和书信体为文学样式,将1980年代知识青年的成长历程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将选调生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个体体验与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开展互文性表达,用纯个性化的“个人档案”唤起公共记忆,以非虚构的真实性记录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独特性,成为时代变迁的一个独特的样本。
从文学表达上,《选调生》既展现细腻温婉的抒情化、诗意化书写,又记录了特定历史阶段西北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鲜活历史场景,极具史料文献价值。
在叙事方式上,《选调生》是复调式叙事结构,以社会实践、乡村治理为主线,以情感追求、恋爱婚姻为辅线,展示了一个既勇于担当、积级进取,又感情丰富细腻的有趣灵魂。
作品对1980年代西北农村的生存状态、政权运作、干群关系、经济发展的记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极具烟火气息的田野考察文本,深刻揭示了深入基层的选调生面临的文化隔膜、信息差异、价值冲突等诸多挑战。
作者初到康县岸门口乡首先必须接纳的是物质匮乏与资金短缺的现状,在建设现代化罐头厂时遭遇资金、技术、交通、信息和观念等的多重阻力。
封闭环境催生了保守观念,村民对新技术、新管理方式存在抵触情绪,改革举措常被视为不切实际。偏远山区缺乏专业人才,医疗资源匮乏;催缴公粮、计划生育等政策落实需依赖村干部义务劳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基层动员效率低下,政策传导不够到位,从而引发干群矛盾;乡政府人力有限,作者身兼秘书、团委书记等职务,难以集中精力推进发展项目;村民依赖零散种养,抗风险能力弱,个体经济难以实现脱贫致富。传统思维固化、行政效能低下、基层治理体系不完善对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选调生而言都是巨大挑战。
但作者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融入基层社会生态,与领导、同事、村民和工厂员工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作,用自己的真诚和智慧化解各种争执与矛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做到了“既要明辨是非,又要让干部群众接受”的良好结局。
作者以建设罐头厂为突破口,彰显了在困境中破局的时代意义。作者基于当地特产栗子鸡的资源优势,提出建设现代化罐头厂的设想,试图将山区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然而,这一可望增加村民收入、改变乡村面貌的构想遭遇资金严重短缺、设备匮乏和技术空白等现实困境。
作者立下军令状,带领团队亲力亲为从落实厂址、筹措资金,到寻求技术支援。历经多次挫折后,罐头厂最终投产,成为陇南地区早期农副产品深加工的示范项目,带动了村民就业与经济增收。罐头厂的建设成功是知识分子理想落地的标志,从纸上蓝图到实体工厂,印证了选调生“将个人成长嵌入国家变革”的价值信念。
在建设罐头厂过程中淬炼了作者的基层领导能力,使其从大学生转型为务实推动地方发展的建设者。建设罐头厂象征着边远山区在时代浪潮中从封闭走向开放迈出了坚韧的一步,成为198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求支点的生动案例,也成为非虚构文学记录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改革的珍贵标本。
《选调生》作为一部非虚构性文学作品,以参与基层社会实践、精神磨砺和思想成长为主线,但同时作为知识青年,爱情生活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郑曦原与恋人李方惠的书信往来,体现两人在理想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支撑。恋人李方惠的理解与支持成为郑曦原克服孤独寂寞和战胜现实困难的精神动力,强化了郑曦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爱情婚恋是《选调生》的副线,主要以书信方式来表达。作品中的爱情副线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书信以细腻、温软的细节性描写充分展示恋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让作品更具可读性和文学性,郑曦原与李方惠的书信往来既表达深沉和真挚的情感也深化了作品主题,使人物形象更加多元立体。
两人的23封书信承载着恋人之间的理解与鼓励,有效缓解了作者的孤独感与迷茫情绪。既避免了主题的单一性和刻板化,又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下的真实困惑与人生抉择。恋人间的信任与承诺将私密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使扎根基层的选择获得情感合法性。
在叙事手法上,作者将社会实践主线与爱情副线并置,也独具艺术匠心。爱情副线虽然以情感生活为主要内容,但并非独立存在,作者将基层生活见闻、人生感受、挫折与成功通过千里飞鸿的方式传递出去,而收获的往往是精神的支撑和心灵的慰藉。
情书的温软、千里之外的理解与支持有效地舒缓了《军令状》的庄严感和暴雨救灾的紧张感,从而避免了文本陷入单调节奏、单一叙事的沉重,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艺术张力。23封情书形成了诗性化的对话空间,呈现了微观个体感受与宏大历史变革之间交流与互动,成为一代青年的成长密码。
《选调生》在叙事艺术上具备了“当时记录”与“当下阐释”的双重时间维度,将“即时性”与“反思性”的交织融合,也将个人档案上升为公共叙事,从而使作品获得历史的纵深感。
《选调生》的创作实践表明,非虚构文学的历史价值不在于追求绝对真实性,而在于通过文学叙事激活田野档案的阐释潜能,使真实获得文学性和艺术性。当个人记忆被赋予叙事形式、情感维度和理论观照时,便获得了参与历史建构的独特力量。
《选调生》通过微观个体折射改革开放初期的宏大变革,体现了个人对历史的精神内省与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其核心在于通过文本的“记忆塑形”,实现自我表达与集体认同的双向建构。
通过社会实践主线和情感副线的复调式书写,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展开互文性转化,在诗意化描述与批判性思考之间寻找张力与平衡,构建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立体历史图景。
《选调生》提供了一种整合个人经历与历史脉络、微观叙事与宏观历史的交融互通的有效路径,深度诠释了的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
作者:翁礼明,云南昆明文理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