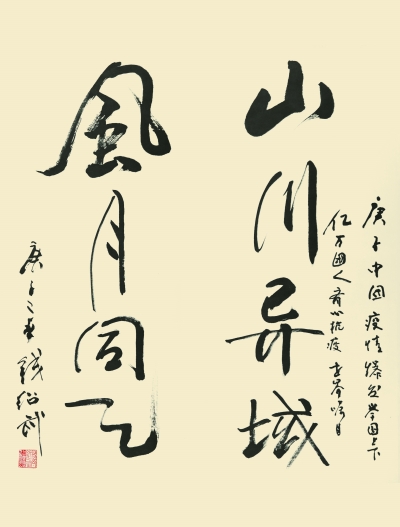读李浩中篇小说集《乡村诗人札记》
关于精神,关于救赎 ——读李浩中篇小说集《乡村诗人札记》
胡永良
读完当代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中篇小说精选集《乡村诗人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可以看到,中篇小说完全能够穿透所谓的“故事”,直抵时代的精神处境。正如篇名中借用“札记”一样,李浩在他的诸多中篇小说中都故意将“故事”揉碎,将原本线性发生的“故事”变成时间与空间的混沌体。这种混沌体的繁复性,使它具备比线性“故事”更丰富的意味性与指向性。
在这里,李浩让它指向了时代的精神处境,指向了心灵的救赎。童年伴随着呵斥、责骂和常常不期而来的暴力,加上自己“捡来的”身世终被暴露,刘义超已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当青春期的反叛意识得以增长,刘义超的反抗终于在父亲刘建亮醉酒睡熟的一个夜晚爆发了。从此,父亲成了他随时可以拿捏与报复的对象,他自己则成为当地臭名昭著的地痞。父亲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没有妻子,在村里不受待见,醉酒、打儿子似乎是他存在感的唯一表达。《故,事》里这样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特殊父子,经受不住生活的磨损。父亲将生活带给他的“恶”无端地传导给了儿子,而儿子又将这份“恶”传导给了社会,并重重地反射在父亲身上。小说的最后,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口口声声巴不得儿子被枪毙的刘建亮,趁天擦黑悄悄地前往县城为儿子送去被子。在这里,我们分明能看到,尽管儿子对他无恶不作,但他心中的善念并没有完全熄灭。
而《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作为一个乡村诗人,面对的则是另一种精神的困守与突围。一个阳春白雪、精神高蹈的诗人,落入骨感、世俗、狡黠、混杂的世界,乡村环境与诗人性格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小说本身强大的张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时代,诗歌与抒情占据了精神生活的至高点,“我的父亲”无疑得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濡染。他身在乡村小学,精神世界却在县里,在诗歌里。“父亲”坚持在本不适合诗人生长的土壤上扎根,注定了他要面对种种嘲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捉襟见肘,面对市侩规则对他的不断侵蚀与挤压。尽管“我的父亲”在县报上发表过两首诗,但他还是被重重的现实所围困,最终,放弃了写诗,进入了麻将室。这是一种精神的死亡。他最后用写春联的毛笔在红纸上写下最后一首诗,然后又独自静静地用墨汁将红纸一点一点涂成了黑纸。诗人“父亲”在乡村的水土不服,无疑是八十年代的狂飙精神在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命运写照。《乡村诗人札记》戏拟诗歌的结构,固执地以“我的父亲,李老师,是一个乡村诗人”作为每节的开头,在重叠反复中构成一种诗的节奏与意蕴,既与小说主题相呼应,与主人公内心世界相映衬,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反讽的意味。
这种精神与现实的纠缠、扭打,是李浩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一种景观。
《藏匿的药片》中的菡子,则时时感到周围的人、事、环境对她精神的侵蚀。丈夫的不忠、每天在药房接触到的患者、同事的爱情悲伤,让她陷入一种如梦似幻的恍惚。她小心地维持着精神世界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平衡,企望自己从这个世界抽身藏起来。当同事于燕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她勉强维持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平心而论,菡子其实有一颗强大的心,她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极力营救,这种努力就像暗夜中的一束亮光。
在《为了,纪念》中,诗人雷马看上去是内心强大的精神生产者,自负,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上世纪八十年代,雷马因为诗歌而受到膜拜,因为诗歌而获得爱,也因为诗歌掩盖了他的放浪与桀骜。他是他那个时代生活的中心。当市场经济大潮来袭时,敏感的雷马立马觉得“诗人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必须最早地感知水的冷暖”。从此以后,诗人雷马结束了,商人雷马粉墨登场。后来,雷马因为经商失败而坐牢,出狱之后的他拿着一叠诗稿来找“我”,但很显然,对于诗歌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平庸的诗作见证了他才华流失后的心灵干涸。雷马是被物欲裹挟而迷失自我的优秀诗人,《为了,纪念》也是诗歌时代的一曲挽歌。
书中八部中篇小说的排列次序,似乎也体现着作者的独具匠心。从前至后,它们逐渐由大地飘向天空,前三篇还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上求证人世的变迁,后面数篇则逐渐向遥远的天空飘逸。从《变形魔术师》至《夏冈的发明》《丁西,和他的死亡》,作者制造着诗一般的隐喻,将读者不断移往科幻的世界,带进狂欢的地带,送入缥缈的星空。也许,这就是小说本身所追求的效果:带读者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寻找精神的新领地。
都市文化界 Dswhj.com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