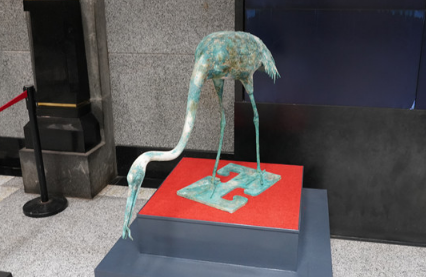梁文彬:书画郎中让文物起死回生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杨佳薇
疫情期间,因为不能出门,“直播”火了,各种各样的“主播”出现在视频里。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古旧书画修复》系列“云讲座”里,聪明睿智当然还有几分幽默的主讲人梁文彬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纸质文物修复师,他自称是“书画郎中”,为观众揭开了文物修复的神秘面纱。
非遗揭秘 文物修复主播开讲
“我其实就是把我的日常工作展示出来,让文物修复不再那么神秘,没想到效果竟出乎意料的好。”说起正在网上热播的、石家庄市博物馆的《古旧书画修复》系列讲座,梁文彬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目前,《古旧书画修复》讲座的理论课程已结束,实操课第一集出来了。”7月6日,身在陕西省三原县博物馆主持馆藏书画修复项目的梁文彬说,“讲座采取线上讲授和实操演示的方法进行。理论讲座部分涵盖古旧书画修复的起源、馆藏纸质文物修复的原则和技术路线等,实践课则涉及书画修复的分析检测、清洗除污、揭展画芯、全色接笔、还旧重装等主要环节的实操演示。视频还在后期制作过程中,由于后期制作需要等待修复体随着天气和温湿度的变化而反复伸缩定性后方可逐步完成,因此,实操课的播出会出现延期与大家见面的情况。录制完成后,我们将继续通过市博物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在线石家庄等平台进行线上更新,市民届时可点击免费收看。”
“纸质文物因年代久远,历经战乱、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加之流转保管不善等多种因素,会使部分藏品出现不同程度的残破、污渍等病害现象。由于纸质文物不便保存、极易损毁灭失,因此抢救性地对濒危级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犹如治病救人,时不我待。”梁文彬说,自古以来,古书画修复技艺属于中华传统技艺之一,有时被民间称为“绝活”手艺,其传承一般都是沿袭师父口传心授的师承制模式,对外是绝对秘而不宣的。本次讲座揭开了古书画修复这门非遗技艺的面纱。
兜兜转转 文物修复还是最爱
成为一名文物修复人,梁文彬自称是“半路出家”。1965年出生的梁文彬18岁就入伍到了武警张家口支队,2004年脱下军装后做起了外贸生意,二十多年来他从事的都是与文物并没有太多交集的工作。
然而,梁文彬与文物修复又有着一种扯不断的情缘。儿时,梁文彬住姥姥家,整天跟着二舅玩儿,二舅会棚壁裱作、扎纸糊裱、剜花剪纸和传统木工、榫卯结构等手艺,二舅是跟同族的一位老人学的,是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
“小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梁文彬说,二舅学艺的时候,他也跟着用剪刀剪纸花,一张纸竟能用剪刀剪出缠枝葫芦、如意云头、喜鹊登梅、携手云子等图案。过年过节,他跟着二舅裱画、吊顶、糊炕厢,“虽然年龄小,我那时只知道打糨糊前要往里边搁花椒水、白矾,打出来的浆糊会很白很细。”
或许,梁文彬对这种技艺的热爱一直根植于心底。他在部队当通讯员时,部队驻地邮局门口有家装裱店,梁文彬到邮局取报纸时便有机会接触书画装裱和修复,断断续续地,他学了手工装裱的部分工序和修复技法。转业后,成为生意人的梁文彬再次遇见了一位书画修复的老师,就这样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他突然就萌生了学习文物修复的想法,最近这几年,他更是放下一切,沉浸在了文物修复的世界里。“真的没有想到,兜兜转转,一切都是缘分,一切仿佛都是注定的。”
脱颖而出 行业中的佼佼者
“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部队教会了我干一行爱一行。决定了要学文物修复,我就真的踏踏实实地学了起来。”在梁文彬看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干好一件事。
刚开始,无论到哪里出差,梁文彬都会寻访当地的装裱修复高手,去人家那里看看,交流学习。文物修复是个技术活儿,光靠自己的学习还不够,必须进入系统深入学习。从2017年开始,具备一定技能和经验的梁文彬加入了中国文物修复师联盟,他便经常向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山东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专家和老师们虚心请教,学习交流,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018年梁文彬开始跟石家庄市博物馆合作,为该馆修复了一批书画,共计15件。梁文彬说:“当时,从保护方案设计一直到修复实施,从修复过程日志,到最后修完形成修复档案记录,都是按照国家文物修复标准化规范来做的。”
梁文彬拿出当年为石家庄市博物馆修复的第一套文物修复档案记录,每张书画都有一个完整的修复档案,跟每个病人有病历一样。“这是方便后来者能看到我们的工作,该补就补,该接笔就接笔,不该接就不接。当时用的检测设备、修复工具、修复材料等,是否符合标准,修复是否可逆,这里都有记录。”
2018年10月,在每省仅限一个参赛名额的情况下,梁文彬代表我省参加了全国首届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其参赛的作品《清代描金宗祠人物画》,从修复前的支离破碎到历经两个月修复后的起死回生,修复效果完美如初,竞赛期间被多家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梁文彬也在全国大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如今,梁文彬已是修复行业中的佼佼者,天津、北京、山东、湖南、福建等地的藏家慕名而来,赶到石家庄找他修复古旧书画。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有人专门找到他,希望他帮忙修复清代的契证一百来张,宣纸材质,有的烂了,有的粘在一起。“请放心,都能修好,没问题。”梁文彬老师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从事古画修复就和郎中一样,大夫见了奄奄一息的病人,不救死扶伤,职业道德不允许,视而不见,也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
书画郎中 很享受“疑难杂症”
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古旧书画修复室里,一堆堆碎纷纷的东西,看着都有点儿让人头大,翻翻,能找出盖印的地方,会很兴奋,“这就是文物修复的乐趣,每每看到这种可以拼接出的落款、钤印或者有题跋乃至具有特殊标记的信息,都让人非常兴奋,说不定就可以修复出某个大家或者大师的作品来呢。完成一件濒危品的修复,就更有一种成就感。”梁文彬说,这些年,他这个“书画郎中”遇到最棘手的“病症”就是“絮化”“粉化”文物,但也能救过来。修复文物一般少说一两个月,最长的甚至半年或一年,考验的是耐心,修复的是爱心。
这些年,梁文彬修复了宋元作品2件,修复的明清作品居多,民国孙中山的对联儿、于右任的册页等纸质文物近千余件(幅)。“看着比较难的书画修复,也是有章可循的。”梁文彬说,一般离不开“清洗除污、润揭画芯、修复补缀、全色接笔、还旧重装”等主要工序和步骤。
“我很享受文物修复中的惊和喜。”梁文彬说,前几年,在修复一件明代绢本书画时,揭开画芯后看到了一根很长的花白头发,“因为此件修复品属于原裱,我们判定是当时明代装裱师的头发掉到了刷糨糊的画芯上。这次是文物修复师跟古人离得很近的一刻,都说我们修复字画是跟古人神交,这根头发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前辈的身影,有了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
古书画修复虽然是有章可循的,但真正做起来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尤其是面对一堆近乎是“废品”的古物,不但要有最基本的修复技能,同时还应具备书法绘画基本功、古文字基础知识和识篆辨章能力、书画鉴定能力。
“其实,纸质文物修复很复杂,所涉及的有物理、化学、生物、植物、纺织、造纸、染料、颜料、色彩学、美术学、书法学、木工、缝纫等领域和相关行业的知识,因此干上文物修复,学习就成了一生的任务。”梁文彬深有感触。这些年来,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梁文彬大胆探索并初步研究攻克了现代印刷品如书籍、文档等“单页双面印刷”的修复难题。然而,他知道,未来,他在享受文物修复的惊喜中,还需要用坚守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修复技艺、践行工匠精神,保护文化遗产”。
都市文化界 Dswhj.com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