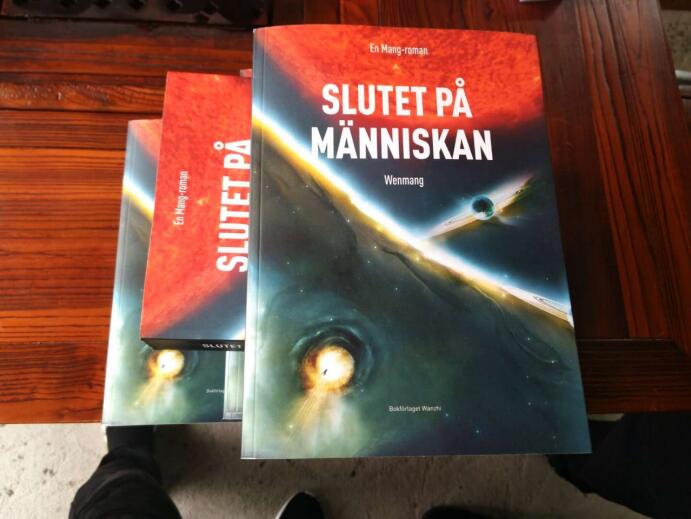“反矫情文学”:不必拿“格调”来压人
近日,随着豆瓣“矫情文学品鉴小组”的走红,网络开展了一场“反矫情文学”运动。短短五个月内,“品鉴小组”便累积了4万多名成员、6000多条帖子,这股风潮还日益发展壮大,在微博等多个社交平台盛行。
“矫情文学”又称“咯噔文学”,指看到后心里会“咯噔一下”。据品鉴小组各路网友整理,“矫情文学”包括“矫情语段”“金句”和“矫情”的文学文本。典型“金句”从泛滥社交网站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到文辞不通的“铁马是你,冰河也是你”……“反矫情”的网友们还罗列了一众下笔具有“矫情”特征的作家,从郭敬明到张嘉佳,分别对他们的作品和句子进行嘲讽、调侃和吐槽。
“反矫情”的理由众多,但大多数人抨击的原因是,“矫情文学”往往过于堆砌文辞,流失了文字用以表情达意的真诚感,言过其实,矫揉造作。而且,诸如“左眼明媚,右眼忧伤”之流的“矫情语段”大多徒显华丽,却常犯基本的语文错误,实在“格调不高”。
但是,当这种对于矫情文学的反感,发展成“反矫情文学”时,事情就有些不太对了。“反矫情文学”的人们,多举出王小波、余华、毛姆等“正统的文学”作为矫情文学的反例,推崇真正“文学性”的表达,并对那些读、写“矫情文段”的人报以嘲讽,鄙弃诸如QQ空间、微博评论中被用滥的、文辞不通的句子。
澄清什么样的文学是格调更高的,是一件好事。毕竟,《红楼梦》之辈和《小时代》之流,无论从文字审美还是思想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要提升社会整体的审美,最起码要先分清楚“什么是好东西”。可是,问题在于,“罗列好作家”“批判坏文字”,不能过于强调格调以至于上升到攻击和贬低人的程度。“反矫情文学”到这一步,就流于铺排名词,标榜“文化”来立道统,这在无形中划分了审美圈层,过于凸显自我身份的“优越感”了——这样叫嚣、贬低过了,然后呢?有什么意义吗?如此“踩低捧高”,并无益于真正规范“矫情文学”的语用,也不能让人们对“文字表意应该有怎样的真情实感”有更多的了解。只谈“你文化格调高不高”,攻击“你读书品位不行”,是最浅表的,还容易因为这样简单粗暴的划分,激起对立的情绪,让双方可对话、交流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说实话,大众文艺审美格调的培养,原非一朝一夕之功力,也不能只把原因归结于看矫情文学的人自身“品味不高、读书太少”。一个人读懂杜诗的沉郁,鲁迅的深沉广博,热爱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艺的璀璨,需要大量的、经年累月的阅读和积累,也离不开从小到大身处的家庭氛围、文化环境的熏染。我们这些普通人培养品位,需要慢慢来,因此社会教育体系对于我们审美素质的形成也很重要。讲得简单点,我们的社会,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让不同地区的孩子都能上一节鉴赏莎士比亚的语文课——这是需要努力,需要时间的事。因此,抛开“你所拥有的、但别人不具备的条件”不谈,只泛泛地鄙视读矫情文学的人格调不高、品味低下,其实是很刻薄的。
而且,文化这种东西,原本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人类在使用和享受文化,因此实在没必要如此强求“格调”,以至于到为格调而贬低人的程度,这大有“形式理性控制人”的越位之嫌。你读郭敬明,我看大冰,他爱奥尔巴赫,我们各自读得都很开心,也许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就是他能读到的最美的句子了,我们可以慢慢普及什么是更好的,但何必恶言相加,攻击和鄙视读这些文字的人呢?不必拿“你品味不高”来压人,也不必基于此而上纲上线,特意搞个“反矫情”出来。我们实在无需让“格调”这种外在的形式,绑架人们真正想从阅读里获得的审美愉悦。文学和文艺的本质,从来都是尊重人、而非尊重格调啊。(红网 李晓璇)
都市文化界 Dswhj.com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