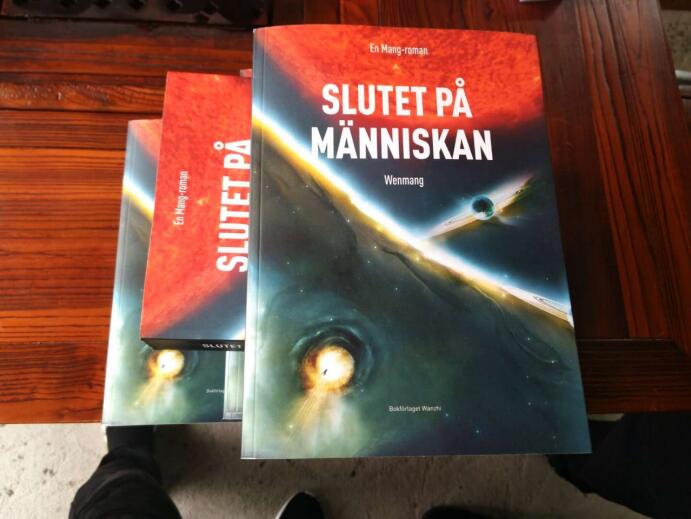发现与记忆:围绕莫干山会议的十年叙事
柳红
一

这是一本并不完整的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文献集,例如,它缺了“以文选人”的会议论文,甚至连论文题目也无处搜寻。曾经试图一位一位地征询,所获甚少,不得不放弃。一些来自北京的参会者,或因参与了会议筹备,像对1300篇论文的审稿等;或因来自中央或国务院机关,或因其他原因属于特邀代表,并非因论文入选。而外地代表,散落各地,时隔三十余年,找寻难度甚大。当初开会,论文本就未要求带上山;而审稿之后的论文有无保存?放到了哪里?亦无人知晓。要知道,这只是几位年轻人创意发起,众多人士和机构支持,举办起来的,虽有名头,但终究是一个民间会议,并非由一个机构统一操持。因而,其资料散失可以想象;正是如此,其会议本身的意义才格外显著。
2019年6月,一些八十年代的青年学人,因日前再次掀起的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在微信群中作了一些讨论。我看到孙方明先生的意见,似可作为本书的一个注释,因此摘录如下:
“十多年来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最大的成果是误导了许多不知情的人,以为价格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和贡献。实际上,莫干山会议的议题涉及到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少建议对高层决策起到了直接间接的重要影响。但是以为一次聚会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方向,那就一相情愿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今天很多人对莫干山会议的追忆,自然含有对美好事物放大的成份。但不争的事实是:一次对全国经济改革有影响的讨论会,主要不是由机构发起的,而是一些个人提议,民间串连,形成共识就开始组织,也没有谁审查批准,居然得到浙江省委的支持和助力,会议过程受到共和国高层的关注和肯定,甚至还委托时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专程到杭州去听取会议汇报。这些黄金年代的追议,是莫干山会议最精彩,也最令人神往的。莫干山会议表明,中青年经济研究者自由自主研究的成果,可以与国家最高层直接对话,可以影响决策。在当时,类似于莫干山会议的大大小小聚会无穷多,而莫干山会因其别具一格,成了旗帜!”
人们对莫干山会及其相关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莫干山会的价值何在?八十年代青年经济学人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是怎样的?他们是怎么样聚合在一起的?又是通过什么管道来影响改革决策的?庙堂与江湖是如何连接的?八十年代的独特性在哪里?等等。
本书分三部分:一是总括性,研究性发掘和回顾会议情况;二是亲历者从自己参会、办会角度来谈;三是历史文献,包括会议文件,工作笔记,日记,报道,照片等。
二
这不仅是一本文献集,也是“莫干山会议”这一事件被发掘和记忆留存的记录。这条线是如何呈现的呢?是通过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编排,由此可以看到整个事件渐次被打开的过程,经由一次又一次书写;一个又一个讲述,像拼图似的,将一小片一小片拼接出大致轮廓。这也是通过民间独立研究、记录,发掘,留存记忆的过程。我格外看重,特别想强调这样一个角度。尤其是在当下,这是我们该做,能做的事,也是某种责任。
先说关于莫干山会议总体性书写部分,从2008年的第一篇到2018年的最后一篇,前后经历了十年。2008年10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了我写的《莫干山会议真相》。其缘起,也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论有关。争论各方都提及了在莫干山会上的争论,然而人们对这个会却鲜为人知。在莫干山会议的四位发起组织者中,黄江南当时在国内,已经接受过采访;朱嘉明和张钢在海外。我与他俩通过skype进行访谈,在写的过程中,也不断追问,请他们确认细节;而另外一位刘佑成,虽四处打听,还是未能联系上,在文中特意说明,并配了1984年年初朱嘉明和黄江南与他在杭州的合影。此外,也采访了一些与会者。文中提及四、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余年,未在报纸上出现过的名字。文章在经济学家圈儿,也在一些八十年代的过来人中产生了反响。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想呈现1980年代的气氛和时代感。那是由很多人,包括青年经济学人群体一齐努力,研究问题,思想激荡,有创意有行动,共同创造的历史。
而莫干山会更大范围地进入人们视野,是2012年曹文炼先生在莫干山发起新莫干山会议以后。一年一度,他不断邀请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参加。从而,使之与历史有某种具体的连接。莫干山会议的故事被反复讲述,以致于成为某种符号和象征。
常修泽先生,既是1984年参会者,也是2012年后新莫干山会的嘉宾,他在2012年所写的莫干山会议史料版,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卓元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料(1949-2011)》一书。它使得一桩曾被彻底消失,八十年代青年经济学人作为整体行动的一个典型事件,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叙事体系。
2014年,在莫干山会议举办三十周年之前,我幸运地得到一些珍贵的私人收藏,像翟新华先生的日记等资料,也做了更多的采访,从而得以写出较六年前更为详尽的会议情况--《历史之棱镜——写在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时》。
时至2018年,收到一位兄长微信转来刘佑成先生所写《莫干山会议始末》。1984年,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基于当时的工作笔记而写,史料价值很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即刻与佑成先生联系,得知他挂笔近三十年,原本此生不打算再写什么,终因捱不住友人相劝,在70岁这年,将经历过的一些事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他拒绝了我提出将文章发表的建议,说既然我做相关研究,尽可以拿去用。我坚持说,要发表了才好引用,要让更多的人读到。《经济观察报》于2018年6月发表了刘佑成先生的文章,并建议我写一个推荐语。我理解,并非是因为我有“资格”推荐,而是出于某种历史延续性和需要点出的意义。在简单介绍了之前的情况后,我写道:
“作为研究者,面对这样的“热闹”,总感到有些遗憾:1984年莫干山会议,渐行渐远,物是人非,存在与会者难免失真的记忆,而纠正这样的情况,将相关研究深入下去,需要有新的和凿实的历史记录问世。终于,封笔二十八年的刘佑成先生“现身”。他以会议主办者的身份和角度,基于当时的工作笔记,写出《莫干山会议始末》,为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了直接、丰富、多元的文献和信息。至此,这一曾经直面社会改革基本问题、掀起头脑风暴、汇聚思想能量,带有时代标志,并为很多人带来崭新历史机会,青年经济学人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一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事件,其残缺部分得以很大程度地填补,其图像更为完整地显现。而这一历史挖掘过程,历时十年。刘佑成先生功莫大焉。”
这就是我想呈现的莫干山会议“发掘史”。
再来看亲历者说。华生和贾康两位是较早回忆莫干山会议的。除了在报刊发表文章或出版回忆录中节选的作者,令人欣喜地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有几位当事人接受了约稿邀请:像时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田源先生;像以工人之身投稿入选,却因工厂不准参会,愤而辞职,前往莫干山的闫卡琳先生;像操持莫干山会劳苦功高的时任《经济学周报》编辑的秘书长张钢先生等,他们都专门撰文。在约二十位作者中,可以看到因为时间久远,有些自己亲身参与的经历忘记了,而较多地趋向于写被众人反复强调的事件。这可能也是某种“记忆”模式,于是,也形成了某种“叙事”。而这种叙事是符合史实的,还是建构出来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正如前述孙方明先生的批评。而亲历者身份、来源的多元化,可以一定程度地增加记忆的丰富性。像闫卡林先生和阎淮先生的讲述,一个是地方工厂青工;一个是中组部青干局官员,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放在一起格外出彩。而孔丹先生,时为张劲夫先生的秘书,与总理秘书李湘鲁先生二人上会,以及在青年和领导之间所做的沟通,则是另外一个难得的角度。此外,我也在学术网站上搜索到一篇文章,作者是1984年大学毕业不久,因论文入选而参会的黄汉江先生所写的回忆。而能够得到刘佑成先生的工作笔记和翟新华先生会议期间的日记,无疑是相当宝贵的一手资料。
伴随着莫干山会议的名声,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和书写,也出现了某些新的问题。例如,当你想尽量揭开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时,总有莫名奇妙的习惯或力量要继续将其掩盖。媒体倾向于强调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人物的角色和作用;而对另一些实际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人物则避而远之。对于这样的现实既理解,又感到遗憾。
本书尊重各位作者的表述,即便有记忆失误,彼此有矛盾处。我想,连同文献集本身,都构成历史记忆与叙事的一部分,而非历史记录和解释的最终版本。
至于莫干山会议的价值和意义,留待读者和历史来评价,来回味。
柳红
2019年7月4日
写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特根斯坦-研究阅览室
都市文化界 Dswhj.com 整理发布